|
“限塑令”落地十载,效果终究如何?
塑料会赢吗?
“限塑令”落地十载,效果究竟如何?真实的答案也许只有垃圾填埋场知道。
纪录片导演王久良把镜头对准了平均使用时限25分钟、降解却需要至少200年的塑料制品。
但在成为垃圾山之前,它是日使用量30亿个、随手可得的塑料袋;它是日流动量上亿个、辗转全国各地的快递袋;它是一天可以垒成几百座山峰、间接喂饱了超过2000万张嘴的外卖盒;它还是农村的“白色海洋”。
塑料在高温中不断变换形态,覆盖了消费社会里每一个个体。10年里,当“限塑令”将“环保有价”的理念推向公众时,科技也不断追逐消费者的环保需求,名目繁多的“环保塑料袋”上了货架、 筛选塑料比重法、降解再生的化学手段等成为大热的环保课题。
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项目是否真正落地,那些“环保塑料袋”被丢弃后又去了哪里。10年过去了,裹上层层面纱的塑料从来都没有缺席。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在官网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就塑料垃圾污染防治建言献策。关于限塑的努力,还在继续。
环保还是商机?
在王久良的镜头里,塑料袋是垃圾填埋场绝对的主角。
50多米高的垃圾山上,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收走了,唯有劣质塑料制品无人问津,其中包括无法统计数量的“环保塑料袋”。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教授刘建国,并不讶异这些“环保塑料袋”的命运。“环保塑料袋需要严格的条件才能降解,比如温度、含水率、特定反应器等,在自然环境下很难降解。”他注意到,这些“环保塑料袋”的去向,依旧是和各类垃圾混杂在一起,再被压缩称重,最终送进填埋场或是焚烧场。
和普通塑料袋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消费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环保需求,多花了一些钱而已”。
他调查发现,大量标有“可降解”标识的塑料袋,其实是降解材料和不可降解材料混杂在一起的产物。出厂后,就加价摇身变成了“环保塑料袋”,那是巨大的商机。
“一个可降解的塑料袋如果沾上油污,那就需要先用化学试剂清洗干净,再进入降解的流程,这个过程又要消耗多少成本?”他说。
王久良很清楚,当下科技进步的速度不可谓不快。意大利开发出新技术――在一堆垃圾里依靠粉碎、比重等方法筛选塑料。但这些手段在中国的推行难度很大。
“我们的垃圾没有进行分类,那些垃圾废水里有什么样的物质,得经过多少道工序、花费多少成本?”他说。
比起把希望寄托在科技上,王久良觉得有更紧迫的事要去做――比如,理性地审视塑料究竟对周遭的世界影响到了怎样的程度。支撑咖啡厅遮阳伞的墩子、道路用来交通隔离的小柱子、随处可见的塑料垃圾桶,目所能及的,处处都有被反复利用后的劣质塑料制品的身影。
回到老家,他发现了一个几乎被塑料包围的农村。儿时离家还未听说过的地膜如今成了农田的“主人”。
“田间地头、渠沟路旁,甚至大街上、农户的院落里,到处见得到废弃的地膜。旧的地膜没有处理完,新的又铺上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很清楚,厚度仅有0.004毫米的地膜很难从土里彻底剥离,由于沾满土灰重量又轻,地膜回收的价值较低,除了焚烧和搁置别无他法。
行走在农田上,如果翻开土壤,肉眼很容易看见碎成一截一截的白色地膜和土块纠结在一起,像是地里长出的庄稼。
他发现,农村是一个几乎“没有管理的塑料世界”。 有环保人士下乡,在老乡家里吃饭,一次性塑料餐具摆上了桌子,用完后,老乡随手就扔进火炉,塑料碗杯速度消失,然后变成看不见的致癌物二恶英,排向空中,再随降水循环到农田和河流。
这些被城市淘汰的劣质塑料制品,随着消费浪潮涌入农村。由于一些乡村没有专门的环卫人员和垃圾回收系统,塑料制品借助风和雨,进入河流或沟渠,留在江河湖海和农田山脉。
负增值产业?
王久良的镜头曾在日本对准过一家回收矿泉水瓶的企业。这家企业拥有一个几百平方米的宽敞车间,拥有先进的智能化和数控设备。在生产线上,塑料瓶依次被粉碎、清洗、回收。车间里,王久良找不到污水,也闻不到刺鼻的气味。
令他意外的是,这样一家“模范”企业的负责人却时常因为回收塑料瓶而烦恼。日本对于污水排放的要求太高了,为了排污达标他们需要花费大量成本。“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我们是亏本的。”负责人告诉王久良,企业每收购一吨废旧矿泉水瓶,政府就给他们补贴2万日元。
即便如此,他们也无力再回收处理更多种类的塑料制品,“环保的成本太高了”。
镜头对准中国垃圾处理厂,却是一幅幅让王久良心酸的画面。他曾花3年时间,拍摄了名为《塑料王国》的纪录片。纪录片里讲述了中国“洋垃圾”的产业链――一些人从远洋货船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垃圾,分拣出可回收利用的塑料,然后经过漂洗后粉碎,进而加热融化,再切割成可供制造业使用的塑料颗粒。
“日本处理一种单一污染物都要建一个厂,在中国一个小作坊却能处理全世界各类塑料垃圾。”他说,“中国有全世界垃圾分类做得最好的人,他们没有防护措施、没有先进技术。”拍摄期间,那些黝黑的面孔教会了王久良分辨全世界塑料垃圾的方法――手感、听响声,然后是看烟看火闻味。
“他们是一群农民。”他说。
一张餐桌大小的粉碎机、两张餐桌长的制粒机就可以组成一家小作坊。机器轰鸣声中,塑料碎屑在空中飞舞。从王久良的镜头看过去,屏幕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见塑料碎屑。镜头再一转,污水可能未经处理就咕噜咕噜排进了河里。
作坊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大小,“你有10台这种机器,而我可能只有1台。”
镜头之外,在日本,更多更难处理的塑料垃圾都被出口到了中国。过去的10余年,中国对洋垃圾的进口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回落以及今年彻底的禁止。
“之所以进口还是有利可图,可真的有利吗?”王久良忍不住反问,“环境的成本算什么?”
3年拍摄时间里,镜头记录下了那些看得见的“成本”,村里的水漂着垃圾和白沫;清洗塑料后的污水流到了林子里;有老太太分拣时不小心碰到了腐蚀品,她的手指整个关节被碳化;有小作坊的老板觉得腰上长了瘤子却死活不愿看医生,“检查出来病咋办?日子还过不过了?一批粒子,娃半年的学费。”
纪录片的拍摄让王久良认清了一个道理,“以环境友好为前提的垃圾回收,都是负增值产业。”他打了个比方,如果环保型回收1吨废旧生活塑料能够产生100元经济效益,需要付出的成本,至少也要101元。“否则,无法解释在被世界公认垃圾分拣回收做得最好的日本,为什么要对企业回收垃圾提供政府补贴,更解释不通为什么《塑料王国》里来中国的洋垃圾里依然会出现日本垃圾。”
有环保人士称,“垃圾填埋和焚烧场挣的是消耗、处理垃圾的钱,而不是循环利用塑料垃圾产生的次生利益。”
事实上,这些干湿混合的垃圾焚烧后发电效率并不高,在不充分燃烧的条件下还有可能排放有毒物质以及产生飞灰和废渣等。但相应地,“从海量的垃圾中回收利用塑料制品的成本更大更夸张。”
“环保很多时候就是几害相较取其轻。”刘建国说,当前社会有一种声音,期待着科学家能够找出完全替代塑料袋的东西。但实际上,从全生命周期计算,无论是帆布袋、纸袋所要消耗的资源带来的污染同样不会少。
他举例说,如果做纸袋,需要经历种树、砍树、做成纸浆、造纸的过程,而帆布购物袋所涉及的棉花种植更是高耗水高耗能的产业,不仅要考虑农药、化肥的使用量,还要考虑土地资源的占用、运输、印染、流通、废弃后填埋焚烧的成本。“你只看到多次使用,却没想过一旦要处理,布袋的重量是塑料袋的几十倍,占用的空间、处理难度都不小。”
这个研究固体废弃物的学者曾做过实验,每使用200次帆布袋,其对环境的影响才能优于使用1次塑料袋。
“根本问题不是去寻找一个塑料袋的替代品,真正要做的,是审视我们的消费行为。”蒋高明说。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
大片的塑料大棚和地膜占领了农田,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数据显示,在短短30年时间里,地膜的使用量增加了200多倍。研究农村白色污染十余年的蒋高明发现,引发蝴蝶效应使农田样貌大变的,跟城里人的餐桌有很大关系。
他说,为了生产反季节蔬菜和水果,农村大量建造塑料大棚。而耕地的“白色海洋”地膜,则是为了改善土壤温度和湿度,以延长经济价值较高作物的生产季节,最终提高其产量。
地膜铺下去后,产量的确提高了。但同时,地膜在使用后很难从土壤里剥离。它们长久地待在土壤里,破坏土壤结构,生物失去了活动空间,线虫、蚯蚓挨个离开,土地最终板结化。
蒋高明注意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人甚至采用了“膜中膜”的方法,大棚盖一层膜,地上再铺一层,为的是不让水分流失,可这样的密封环境会活活地把土壤里的微生物憋死,最终演变成脆弱的生态系统。
他看到了一个又一个伤心的面孔,一些农民都遭遇了作物烂秧、病害等问题,有牛羊吃了地膜覆盖下的花生秧子,竟被活活憋死。蒋高明叫人翻开土地,清晰地看见地膜缠在花生的秧子上,像是寄生在秧上。他们把土壤带回实验室检验,甚至发现了30年前残留的地膜,“它已经变成微小的、肉眼不可见的塑料片了,但并没有消失”。
来不及处理的地膜大多付之一炬,因此产生的六氯代苯、二恶英、多氯联二苯等有害物质由此进入空气。
而那些染病、使用过量化肥和农药的作物去了哪儿?蒋高明说,“最后都上了城里人的餐桌。”
他觉得这一切很讽刺,无穷无尽的消费需求控制着市场的流动变迁,却又最终被其反噬。他曾和农民讨论,干脆把果园里铺了一地的反光膜撤走、少用,以减少污染和浪费。可对方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很简单――不用反光膜,苹果上色不均匀,卖相太差,没人会买。
“苹果是拿来吃的,不是拿来看的。”蒋高明说。
这位学者忍不住反思,“我们真的有这样大的消费需求吗?”他反感一颗糖一张塑料纸的包装模式,公开批判出版业给书贴塑料膜的行为,也反对酒店提供一次性塑料洗漱用具,“这会造成多少浪费?”
刘建国总结了12个字:“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
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办公楼向外看去,密集的住房和写字楼正在不断压缩着城市的空间。塑料袋、建筑垃圾、电子垃圾、废钢铁、轮胎、玻璃,甚至包括共享单车……刘建国觉得,经济增速太快了,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改变,需求被刺激,催生了快捷市场。共享单车一两年前还是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天使”,转眼间就在小区、停车场垒成了垃圾山。
“很多人不思考,只觉得塑料袋是个大问题,所以一边儿吃着塑料盒包装的外卖一边儿痛骂塑料的罪恶。真正思考了,你会发现处处都是问题。”这名学者叹气道。
大拆大建后废弃的建筑垃圾填埋场,也曾是王久良镜头捕捉的对象。他在一个近两公里宽的填埋场看到了密密麻麻的人。高峰时,两千多人在各种废旧管材、线材、塑料、钢筋、砖头里穿梭,抱着东西就往填埋场边上的窝棚跑去。那是他们的暂居地,也是废弃材料的暂居地。起重机和卡车很快会带走这些材料,再送往下一个工地或是工厂。
一派热火朝天的气氛里,王久良在远处站着,五味杂陈。
在拍摄《塑料王国》时,这名年轻的纪录片导演注意到了一组数据,从1995年大规模进口洋垃圾到2008年左右,整个洋垃圾回收产业反映在经济价值上都是一条完美向上的曲线。美国1吨9美元的垃圾,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后,能以上千元的价格卖给小作坊,经过处理后,一吨塑料颗粒的售价甚至直逼五位数,价格“快赶上原材料了”。
“我以为人可以低到尘埃里,却没有想到能低到垃圾里。”一次放映活动上,一位大学老师看完影片后哭了。
要让企业感觉到疼,要让民众感觉到疼
很多时候,王久良觉得自己也被消费主义的浪潮裹挟了。他用手戳了戳手中的塑料杯,反问道:“如果不提供塑料杯,是不是就不能喝饮料了?”
王久良说,生产多少塑料,最终就会有多少塑料垃圾出现,不断重复利用的过程只会让塑料的性能不断递减,终究会变成真正不可回收利用的塑料垃圾。而想要规避塑料垃圾的环境污染,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使用。
在他看来,“限塑令”目前的范围太窄了,“应该覆盖更多的产业”。而手段需要靠政府来调节,“生产矿泉水瓶的企业获得了利益,是否应该承担环保的代价?民众享受到了塑料瓶的便利是否也应该为此买单?包装行业是否应该改革?超市售卖塑料袋要不要缴税?”
“要让企业感觉到疼,要让民众感觉到疼。”他说。
刘建国认为,过去的10年,“限塑令”最大的价值不在于限制了多少超薄塑料袋的产生,而是它通过对塑料袋收费,向社会传递了“资源有价,使用资源需要付出成本”的信号。
只是,“如果有朝一日塑料餐盒真的从5毛钱涨价到5元,消费者愿意掏钱吗?有朝一日,真的用回收废物造出了可循环餐盒,人们愿意使用吗?”他说,成本增加、市场振荡,企图一下子改变形势是不可能的事。
这位学者认为,当下需要为塑料正名,“材料不是从天而降的,塑料没有罪恶,它是被人类制造出来的。”
“塑料不应该被妖魔化,更不应该把塑料的罪恶和管理不善的问题混为一谈。”他说,“我们能不能做到不让塑料进入水体?不让它进入农田?任何材料管理不善都会成为问题,不只是塑料。”
“提高整个回收处理系统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推广垃圾分类,这是能实实在在做的。”刘建国眼中的突破口是农村,“要无中生有,尽快建立基本的回收处理系统,哪怕是简易的填埋场。”
如果能做好分类垃圾让处理难度降低,那么就有可能建立衍生的塑料分类中转中心,“起码会比一把火直接烧了更有价值”。
但在蒋高明看来,眼下可以去尝试的事情,不止这一点。
曾经他听闻,在缺水的甘肃,有农业学家帮本地农民开发出了双层地膜,在土地铺上两层地膜,目的是帮助干旱的土地锁住水分,以便种植更多的玉米。这个项目拿下了课题,最终“各方满意”“皆大欢喜”。
蒋高明却一点也不开心,“技术出了问题,你想的是再开发一个技术来解决。实际上,人为制造最佳温、湿度的环境来种植玉米,都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他说,“源头就错了。”
此前,有西班牙科学家发现,100只蜡螟在12个小时内降解92毫克的聚乙烯,被媒体编译后,这种虫子成了具备消化塑料能力的“救世虫”。新闻一出,蒋高明哭笑不得,人类每天生产几十万吨聚乙烯,让虫子来吃不知道要吃到猴年马月。更重要的是,让虫子去吃自然界原本没有的东西,这个想法依旧“走偏了”。
他总在思考,也许甘肃部分地区的自然条件不适合种植玉米,是否可以开发种植中草药?是否能想办法推进生态农业呢?
蒋高明很清楚,能够真正让这一切改变发生的,是消费者。“城市消费者手中的钞票就是最好的选票,你投到哪里,哪里就会形成产业。”他说。
我们该怎么办?乐观点!
在拍摄《塑料王国》和《垃圾围城》之前,王久良是中国传媒大学的科班生。那时候,有些“意识流”的他想做一个名叫《超级市场》的展览,“一种概念化的东西,货架上摆满的不是新商品,而是摆满喝完牛奶的空盒子,吃完冰淇淋的塑料桶什么的,让垃圾填满货架。”
想法冒出后,他开始扛着机器往大大小小的垃圾场跑。可在那里,他发现了比艺术更重要的东西。塑料垃圾问题的严峻性远远超出了这个年轻人的想象,“有更迫切的事情需要你去解决”。
在现实面前,形而上的概念艺术落地,最终变成了一个纪录片项目。他也抛弃了含蓄的观点表露,选择直指问题。
《塑料王国》在后期制作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思考:表面上看,这些产业在当地可能是支柱,养活了数不清的农村家庭。但当个体利益的获取建立在损害他人的利益基础之上时,这又变成了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砍掉这个行业是必须的,要看到更多受影响的人,他们的利益谁来保障,谁又去发声?”
他始终忘不了拍摄期间遇到的一位老人。因为处理“洋垃圾”,拍摄的村子水源受到污染,附近的村民只能走远路去买水。一天,王久良在买水的地方碰到了一位佝偻的老太太。商贩告诉老人,一桶水4块钱。老太太很不好意思地开口,“4块钱,我能先欠着吗?”
今年1月起,国家开始全面禁止从国外进口24种“洋垃圾”,砍掉了这个盘桓20余年的产业。王久良从中看到了希望,他想,如果真的征收垃圾税、自上而下地去推动改革,也许希望就在前方。
蒋高明认为这不算难事。他记得过去国家层面对地沟油、面粉增白剂的整治,每一项都是动了不少人的蛋糕,可最终都得以推行。
这一次,难啃的骨头变成了塑料制品。
“英国女王可以自省,要求王室产业内禁止使用塑料吸管和塑料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他说。
英国今年年初曾向公众承诺,英国政府将实施25年计划,在2042年前消除所有可避免的塑料垃圾污染。而这一发声没能得到普通民众更多的支持,很多人在社交平台上留言,“政府把时间设置得太晚了,2042太晚了,现在就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塑料问题成了世界级难题。孟加拉国曾遭遇一次灾难性洪灾,人们惊讶地发现,塑料袋竟然是排水系统堵塞的首要原因。无法统计数量的蓝脚鲣鸟也正在失去自己的家园,塑料垃圾成了秘鲁罗伯士・泰拉岛海滩新的主人。有数据显示,这些塑料垃圾造成每年数十万海洋动物的死亡。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说,“在英吉利海峡捕获的鱼当中,每3条就有一条含有塑料碎片。”南极同样没有摆脱塑料污染的灾难,今年年初,科学家发现南极的表层海水里出现了肉眼不可见的塑料微粒,含量甚至高于海洋中的平均水平。
孟加拉国在2002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施塑料袋禁令的国家。法律规定,进口或销售塑料袋的人可被判最高10年徒刑,发放塑料袋者则被处以6个月的监禁。如今,这个国家的超市里只会售卖布袋和纸袋。
王久良带着片子在世界各地巡回放映,许多年轻观众看完后会忍不住向王久良发问:“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问题他不打算回答。王久良希望这些关注环保的年轻人自己去寻求答案。
也有年轻人问他,拍了这么久的垃圾,会不会特别悲观。王久良笑了,“当你还在坚持做这件事的时候,就说明那颗想要改变的心没有变过。乐观点,就算我们不行,还有孩子们呢。”
这几年,让他惊喜的是,在民间已经有了许多关注垃圾回收的团体,在地图上像星星点点一般冒出,寻找着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在无锡,一群医生和大学生组成的团体关注废旧注射器等医疗垃圾的回收问题。他们把无锡的各大医院跑了个遍,劝说对方接受自己的提议――向每一位需要在家使用注射器的病人发放特制的利器盒。这个盒子被用来专门放置使用后的注射器,病人使用后可交回医院设置的回收站点,从而避免了注射器直接被扔进垃圾桶。后来,他们又一路跑到苏州、上海的医院。
这项事业,如今还在推进之中。
京东物流绿色包装项目负责人也坦诚,塑料快递袋用量极大,一次性包装在成本上有很大优势,目前在快递行业依然占据主流。“推行循环快递包装在社区末端回收存在困难,包装回收体系和社会基础设施不健全,也缺乏法律法规来支撑回收企业进行回收。”
眼下,京东物流正在推广使用循环快递箱――青流箱,采用PP材料,可以回收多次循环使用,破损后可再造新箱子,对环境不造成危害,能够替代一次性纸箱。他们希望,“协同社会各环节资源,形成较完善的产业链,将绿色循环包装全面落地。”
刘建国说,包括塑料袋的问题在内,中国的很多问题都集中在超高速的经济发展上。这些问题很多发达国家用了上百年才逐步解决的,而中国需要在2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去解决,他希望民众能给予多一点支持和理解,同时也能从自身出发,更全面理性地看待自己的消费行为,反思自己的消费需求。
“其实就是人类走了一段弯路而已。”蒋高明说,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及时纠正就好。他甚至希望,有关塑料袋使用、滥用、限制、反思以及今后的种种都能被记录下来,写进教科书,成为历史里永远的一面镜子。 来源:中国青年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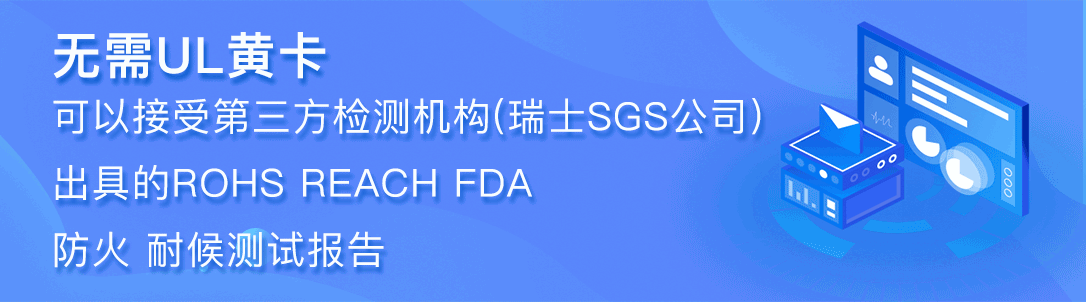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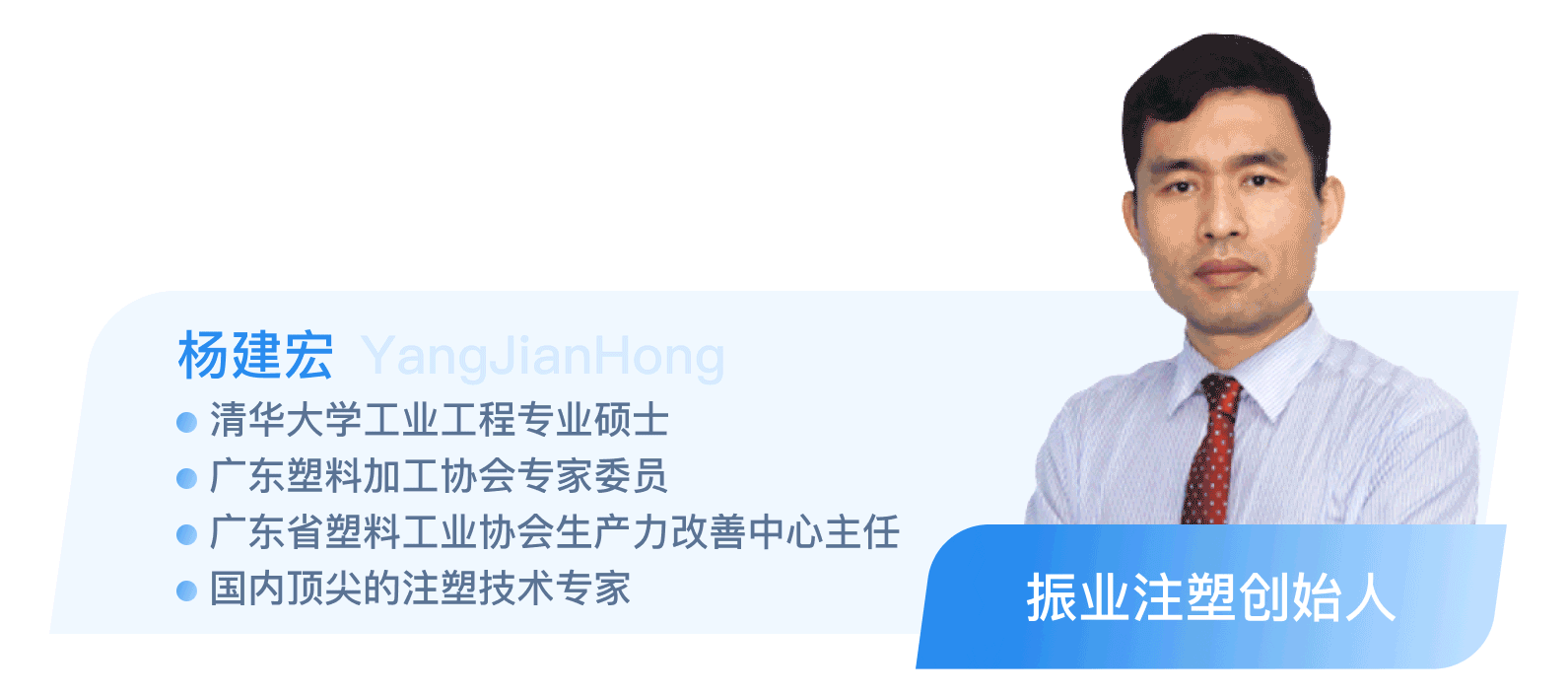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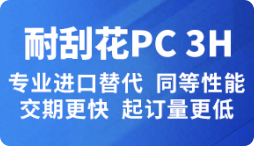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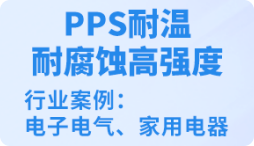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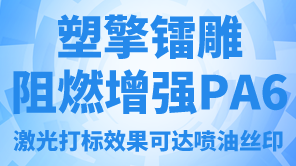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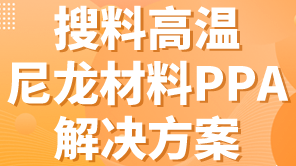




















 支付宝
支付宝 微信支付
微信支付